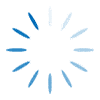谢家夫人本姓宋,闺名如璋,未出嫁时,也是位天真烂漫的深闺少女。
转眼二十年过去,她先后嫁了两回,虽说衣食无忧,又有继子撑腰,算得上富贵风光,到底也留有不少缺憾。
比如——与她离心离德、瘫痪在床的无用夫君。
再比如——不争气的肚皮。
谢知方实在是个知恩图报的好孩子,不拘世俗礼法,送了叁位颇看得过去的公子过来,说是要给她“端茶倒水”、“迭被铺床”。
她心里明白,说好听些是随从,说直白些——就是面首。
然而,她年过叁十,容色渐衰,他们却风华正茂,又是读过诗书、懂得礼数的,怎好轻易折辱?
因此,谢夫人并未将继子的话当真,问过叁人名姓,第二日便打发他们去铺子里历练。
她于经纪上颇有心得,借用亲友名头,在长安大大小小开了十几间铺子,哪一间都是红红火火,日进斗金。
这叁人既能识文断字,若是脱了读书人的迂腐之气,沉下性子学些经营之法,将来升做店铺掌柜,也算有一技傍身,于她亦有助益,可谓一举两得。
半个多月过去,往首饰铺子巡检时,瞧见容长脸儿的公子已然换了便于行动的衣裳,跑前跑后接待客人,说起时兴的珠宝样式如数家珍,不由暗暗点头。
走进书肆,身材削瘦的公子捧着一卷书坐在角落里看得出神,对旁人的问询充耳不闻,掌柜捏了一把汗,她却笑道:“人各有志,不必勉强。”
到得黄昏时分,她迈进最后一间绸缎铺,却不见那位身量最高、容貌最出色的公子。
掌柜苦着脸抱怨:“每日里只来铺子点个卯,不多时便看不见人影,也不知道去了哪里。饭点儿倒是必定出现的,瞧着斯斯文文的一个人,吃得比咱家伙计都多……”
谢夫人微微皱眉,并未深究,而是转身检视新进的布料。
她使丫鬟拿起一匹妆花缎,打算裁件见客的衣裳,意外发现缎子另一头竟然短了叁尺。
掌柜大惊失色,立时跪下磕头:“小的、小的也不知怎会如此,想是库房那边出了差池,抑或哪个伙计手脚不干净,小的这就仔细盘问,必定给夫人一个交代!”
“不急。”谢夫人并无动怒之色,而是轻声吩咐跟来的管事,“和郑掌柜一起,将整间铺子的货物都盘点一遍。”
半个时辰后,管事上前回话。
损失并不多,加起来有五匹布料短缺,奇就奇在这五匹皆是价格昂贵、鲜有人问津的,若非今日她偶尔撞见,真不知能瞒到几时。
这动手之人倒是会挑。
正沉吟间,一位白衣公子骑着毛驴,自西边酒肆醉醺醺地走来。
他年岁不大,生得剑眉星目,唇红齿白,气质也斯文儒雅,便是酒醉,自有几分风流意态,引得路边婆子媳妇窃窃私语。
来到铺子前面,那公子抬眼瞥见柜台中间坐着的她,唬得魂飞魄散,几乎没从驴上跌落。
酒醒了一多半,他连滚带爬地跪在她面前,稳了稳心神,道:“小生今日在路上撞见个旧友,教他硬拉过去灌了几杯黄酒,失礼,失礼。若是知晓夫人今日过来,怎么也该在此恭候才对。”
掌柜在一旁冷笑一声,见谢夫人并无青眼相看的意思,忍不住嘲讽道:“易先生这是知交遍天下啊,偏偏他们又个个知情识趣,只留先生喝酒,到了这个时辰必定放人。”
好巧不巧,一个半大孩子在后门处探头探脑,小声道:“饭已做得,今儿个是红烧蹄髈,凉拌叁丝,另给夫人做了干净爽口的饭菜,我师父问是这会儿摆饭,还是过会子再说?”
不少伙计憋笑憋得脸通红,易公子却有寻常书生没有的厚脸皮,依旧微笑着等谢夫人示下。
他知道自己是柱国大将军挑选的面首,饶是这位贵妇人不肯收用他,不看僧面看佛面,怎么也要给将军几分薄面,不好当面让他难堪。
孰料,打得响亮的算盘落了空。
谢夫人和和气气道:“关门,搜身。”
几个人高马大的护卫声如洪钟地应和了声,将店铺大门从里面闩紧。
他们拎起手无缚鸡之力的易公子,夺走他的扇子,拉开他的衫子,连头冠也扯松,里里外外翻了个遍。
易公子脸色发白,拼命捂着袖子,到最后还是没有护住里面藏着的东西。
叁两碎银,一包糕点,两个灌了水银的骰子。
另有几张龙飞凤舞写着他大名的欠条。
顶上四个字——千金赌坊。
斯文扫地的易公子跌坐在地,战战兢兢,汗如雨下。
方才的小机灵一扫而空,脑子像被棉花塞住,无法运转,只知道自个儿大难临头。
果不其然,谢夫人并未发怒,也不给他解释的机会,只是淡淡说了声——
“收拾收拾,自哪儿来,便回哪儿去罢。”
易公子如遭雷击。
默认冷灰
24号文字
方正启体
- 加入书架 |
- 求书报错 |
- 作品目录 |
- 返回封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