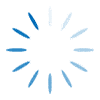谢知方如蒙大赦,因着荆条太长不便行动,只好就地卸下,挑了根最粗最结实的,弯腰钻进马车。
他就势跪在谢知真脚边,因着害怕尖刺伤了她柔嫩的肌肤,用帕子将荆条裹好,腆着脸塞到她手里,这就要宽衣解带,露出后背给她鞭笞。
谢知真连忙喝止了他,轻轻叹了口气,道:“你没瞧见我留下的字条么?”
“甚么字条?”谢知方一脸茫然。
“我今日是要去庙里还愿,并非出家。”见弟弟趁她不备往跟前蹭了蹭,打算如往常一般耍赖抱腿,谢知真抬起一只玉足抵住他的胸膛,“与两位夫人约好了的,早上见你睡得熟,便写了张字条,压在枕头之下。”
显然,谢知方一觉醒来,发现她不见了踪影,六神无主,越想越歪。
思及此处,谢知真的心又软了两分,将荆条掷到一旁,说道:“梵刹寺离此地不远,说话间就到,有甚么话,等回去再说罢。”
得知她并不打算断发出家,谢知方长松一口气,握住纤纤小小的脚,隔着绣鞋亲了两口。
见她背转过身,和衣躺在榻上假寐,他也不敢说话,老老实实跪在一旁守着。
一刻钟后,马车渐渐停下,谢知真避开弟弟的搀扶,踩着杌子下了车。
有谢知方在,知府夫人与同知夫人不便靠近,远远地行了个礼,在僧人的指引下前往放生池。
走不多两步,同知夫人暗自庆幸,说道:“我瞧着侯夫人成婚多年,膝下无所出,又听说她早些年身子不大好,想着许是损伤了根基,正打算送两个好生养又老实的丫头,好博他们二人喜欢,万想不到侯爷惧内至此!”
“快消了你的主意!”知府夫人连忙摆摆手,“我也有些纳罕,夫人金贵柳质,雅静温柔,怎么侯爷竟怕成那样?难不成有甚么独门秘传的驭夫之术?改日说不得要讨教一二……”
且不提两位夫人在背地里如何猜度惊叹,却说谢知方亦步亦趋地跟着谢知真来到大殿,平日里喋喋不休的人这会儿成了个锯嘴葫芦,只一味里扮可怜,瞧姐姐脸色。
谢知真虽不驱赶他,态度却着实冷淡,与迎上来的住持轻声寒暄几句,捐了一千两银子的香火钱。
“一千两怎么够?捐五千两!”谢知方正愁找不到献殷勤的机会,见状立时放出豪言,往身上摸索时才发现并未带银票,存了大半身家的信物也在昨晚送给了姐姐。
他一时僵在那里,颇有些下不来台。
耳听得小沙弥们小声嘲笑他胡吹乱嗙,于佛祖面前打诳语,就连住持慈眉善目的笑容都好像蕴含别样深意,谢知方脸色青一阵白一阵,根本不敢去看姐姐的表情。
谢知真侧过脸对枇杷道:“再替母亲捐四千两银子,供一盏长明灯,也算是我的一点孝心。”
加起来正好五千两。
见姐姐不动声色地替自己解了围,谢知方愣过之后不免大喜,嘴角几乎咧到耳后根,连小和尚们非议他以色事人的话都不觉得难听,反而沾沾自喜,得意洋洋。
点过明灯,谢知真屏退左右,偌大的佛殿中只余姐弟二人,接着轻提裙摆,端端正正地跪在观音菩萨前的蒲团之上。
谢知方是经过鬼神之事的人,并不敢怠慢,跟着乖乖跪下,发了些夫妻恩爱、缘定叁生的愿望,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背对他的窈窕身影,目光狂热且执着。
见姐姐低声吟诵了几句,伏地叩头,他连忙重重磕了叁个响头,走上前扶她起身。
“姐姐说这一趟是为还愿,还的甚么愿?上一回是何时来的,怎么我竟全不知情?”一半是出于好奇,另一半是为着引她开口,谢知方出言发问。
直到走出烟雾缭绕的大殿,谢知真才缓缓答道:“两年半之前,父亲骤然得病,我从临安赶回长安之时,路经此地,许下一个愿望。”
不知为何,谢知方的心忽然提到嗓子眼,呼吸也有些发紧。
他定了定神,问道:“甚么愿望?是……关于何人的?”
谢知真转过身看向弟弟,片刻之后长睫低垂,轻声道:“那时候你在辽东苦战,朝中局势又变幻莫测,我求菩萨保佑你平安归来,早日远离是非之地。”
彼时她只拿他当弟弟,明知他怀有非分之想,明知他手上染满鲜血,却还是牵挂着他,却还是难以克制担忧的心情,特地上山为他祈福。
谢知方忽然说不出话,眼角发酸,喉咙哽咽。
他上前一步,轻轻拥住她。
春日已至,干枯的树枝上绽出新叶,寒冰消融,拂过脸颊的风也是暖的。
谢知真靠在弟弟怀里,被他身上的气味裹着烘着,有些昏昏欲睡。
“姐姐,无论发生何事,在你心里,我总是最重要的那个,对不对?”如果说早上醒来,发现铸成大错的他内心的愧疚有十分,这会儿便翻出数倍不止,因着心疼她,因着永远无法还清的亏欠,恨不得找面墙壁一头撞死。
谢知真微微点头,拍了拍少年挺拔的后背,声音里带出一点儿委屈:“我说过许多次,可你总是不信。”
“我信……我现在信了。”谢知方声音颤抖,情不自禁地将她拥紧,“姐姐,在我心里,你也是一样的,再没有人能比你更好,再没有人能让我疯成这样。”
他顿了顿,又紧跟着认错:“我知道发疯不好,可总是控制不住自己。昨晚那般欺负你,而今只觉无地自容,姐姐若是能如数年前一般使人打我一顿板子,我心里或许还能好受些……罢了,罢了,就算断手断脚,也难以弥补姐姐受到的伤害,我……”
他说着说着,又掉了眼泪,鼻子通红通红,俊脸皱成一团,依稀有些小时候撒娇撒痴的可怜样子。
谢知真的心化成一滩春水,拿出帕子替他擦眼泪,忍不住刮了刮高挺的鼻梁,臊他道:“都几岁了,怎么越活越回去,玩起一哭二闹的把戏来?真当我拿你没有法子?”
她知道他病入膏肓,再难拉回正道上来,而这难缠的症候,有八九成出在她身上。
到底是打断骨头连着根的亲弟弟,舍是舍不下的,又不可能塞回娘胎里回炉重造,是好是歹,她都得接着。
“快把眼泪擦一擦,咱们回家好好说话。”到底是佛门清净地,不好太过亲密,谢知真推开弟弟,垂首替他整理衣袖,态度软和了许多,“很多事并非你想的那样不堪,我……我写和离书,也与裴公子无关,完全是在生你的气。”
理解了她寥寥数语隐含的意思,谢知方吃惊地睁大眼睛。
默认冷灰
24号文字
方正启体
- 加入书架 |
- 求书报错 |
- 作品目录 |
- 返回封面